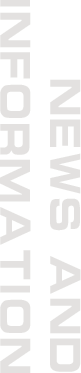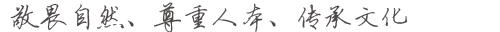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张晓玲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后透露,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14个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将于今年完成,开发边界将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定,不得超越界限盲目扩张。
防止大城市扩张,是很多国家在发展中都曾遇到的问题。如今,他们通过种植绿带、禁止在城市边缘开发等方式,有效保护了城市边界不被破坏、防止了城市过度扩张。
加拿大“精明增长”限制城市边缘开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溪发自温哥华 “如今的家园不说变得面目全非,也让人看着颇觉有些眼生,而且变得越来越热闹。”与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紧邻接壤的南素里和白石两市当地居民近来经常这样反映。近年来,随着移民人数剧增,加拿大各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砍伐森林、拓宽道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尤其前几年兴起的大陆华人投资移民潮,使得拥有“最宜居地”之称的大温哥华地区新潮住宅、精美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城市,在不知不觉中“变胖”了。在加拿大,政府从来没有依仗地广人稀的优越资源掉以轻心,相反长期以来一直依法严格管理土地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加拿大城市化进程,要求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的概念写入城市开发计划内。而对规划实施方面的考虑,主要包括技术分析和分区评估两方面。技术分析层面,加拿大土地按地点被划为不同用途,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甚至想砍棵树,都要改变规划,起草新的规划书,向市府报批并备案。但正是这细致繁琐的法律程序保证了建筑的合法性以及市貌的统一规划性,也避免和减少了大家“踢皮球”。
加拿大是先进的现代化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农地和农民利益,若是农民不点头,谁也别想征他的地;有些农地甚至被划为不可进行商业开发的重点保护区。
加拿大农村与城市间差异十分模糊,很多农民其实就是“城里人”,因为他们的农场牧场就在城市一角;有的农田居然把城市拦腰截断,想从城南到城北必须经过大片农地。有意思的是,有人搬进新居,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居然看见邻家马匹正把头伸到自家后院,跟自己这个“新来的”打招呼,这都基于房屋开发商把房建在牧场边上。
不过,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加拿大人不得不向土地要房子,市内尚未开发的林地和偏远地区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首选,曾经冷清寂寥无人问津的城市边缘,如今变做人丁兴旺的时尚大都会,城市“变胖”不可避免。为有效控制城市无限蔓延、使城市发展边界受到控制,政府提出另一有效策略:对棕地——市区内被重金属等工业污染的土地进行治理。
房地产商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会自觉将目光转移到棕地开发,自然也担起污染清理和资金筹集的任务,成为棕地开发的主力军。这也掀起了规划领域的所谓“精明增长”运动,主要就是限制对城市边缘区的开发。具体可以通过对农业地区规划,在城市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改造原有的工业港口用地以及提倡“新城市主义”,提高土地的使用密度来实现。
别看现在加拿大城市发展边界控制做得很出色,曾经在二战后,美加两国都曾一度放任新城建设导致城市畸形蔓延。惨痛的教训让加拿大人学会扩城筑舍总以考虑如何避免对自然景观的冲击为先。
加拿大目前在规划方面也多少面临着世界各国大城市共同的问题——正以低密度形式不断向外扩展。这促使加拿大省政府想出将一些市镇进行合并,形成所谓超级城市的“妙招”,但是边缘小镇和村庄逐渐衰落,而乡村区域也缺乏活力,备受诟病和非议。
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论,不用担心城市会变成一块越摊越大的饼,而耕地也不会日益瘦身。
日本城市边界禁止开发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蓝建中发自东京 去过东京、横滨等日本中心城市的人无不感慨日本都市规划布局合理、交通便利、生态自然。人均可利用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很紧张的日本,不仅建设了世界三大都市圈之一——东京圈,更保持了城区周边的田园风光,生产、生态、生活区错落有致,立体分布。
这与日本实施的“都市计划”有很大关系。1919年,日本就制定了《都市计划法》,1968年,该法更新。新的《都市计划法》制定了开发许可制度,规定了城市计划限制等必要事项。
《都市计划法》明确规定了“都市计划区域”、“市街化区域”、“市街化调整区域”等开发细节。比如都市计划区域是指“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综合建设、开发和保护的区域”,“都市计划区域”占日本国土的25.7%,却居住着全国96.1%的人口。“都市计划区域”由都道府县政府指定,如果横跨数个都道府县,则由国土交通大臣指定。
都道府县政府在认为有必要为了避免无序的城镇化而有计划地建设城镇时,可以在都市计划区域中区分“市街化区域”和“市街化调整区域”。在“市街化调整区域”,原则上禁止开发行为,除了现有建筑物之外,整体上都要作为农林水产业的田园地带。不过,可以建设一定规模的农林水产设施、公共设施等。
日本各个政令指定都市(被认为有必要限制城市规模的都市),既存城区均被这些“田园地带”所环绕,国土交通厅《国土调查·2008》显示,此部分的面积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10.3%,东京圈两大核心都市,东京及横滨的市街化调整区域的面积占市域的比例分别高达39%和26%。
日本能够完成这样的城市规划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政府掌握土地的开发权,政府沿既有城区划出一条环状地带,此地区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不批准开发申请即可。
2006年5月,《都市计划法》修改后,限制大规模商业和娱乐设施到郊外开店。为此,《建筑基准法》也随之修改,规定占地超过1万平米的,在大规模商业和娱乐设施中,原则上只有为附近居民服务的商业设施、一般商业设施以及没有污染的“准工业设施”才允许在郊外建设。
欧洲用绿带限制城市扩张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林吉儿发自曼彻斯特 翻开欧洲大陆地图,各色密密麻麻的分界线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因为历史上,欧洲一直是小国分裂来分裂去,使得欧洲大多数城市面积较小,布局紧凑。追溯到古代分封制,欧洲形成过很多单个城堡和城邦,出于安全考虑城市大多都以城墙或城墙的另一种形式——陵堡围护。随着铁路、汽车的出现,城墙成为交通障碍。到18、19世纪工业化革命,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突破封闭城墙围绕的空间范围,因此城墙逐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规划概念:著名的“绿带政策”——之前城墙占用的土地被改造成环城绿带,作为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边界。所谓“环城绿带”,是在一定城市或城市密集区外围,安排建设较多的绿地或绿化比例较高的相关用地,形成城市建成区的永久性开放空间。早在1580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发布了绿带构想公告。193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伦敦及附近各郡的《绿带法》,并通过国家购买城市边缘地区农业用地来保护农村和城市环境免受城市过度扩张的侵害。伦敦的环城绿带建设是英国城市规划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世界绿带模式典范,被许多国家城市效仿。其他像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也是绿带建设相当成功的国家。
环城绿带之所以在欧洲被广泛应用,与近现代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直接联系。工业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同时导致一系列“城市病”(失业激增、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其中1930年12月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被列入“20世纪最为著名的由环境污染造成的八大公害事件”。而环城绿带正好有效地抑制了这种趋势。可以说,欧洲是在反思和解决“城市病”的实践中丰富了城镇化理念和法规。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根据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的理论以及20世纪沙里宁的有机疏散方针,确定了建设新城,疏散伦敦中心区人口的对策。经过哈罗新城、朗科恩和密尔顿·凯恩斯三代新城之后,如今伦敦中心区的拥堵已大为缓解,而新城周边的大片永久性绿地保证了城市的环境质量。
在新城建设过程中,英国还有效利用了各项技术革命和规划理念革新,前者如轨道交通体系的大量运用,后者如旧城区的再开发利用。经过半个世纪,城市经济圈由封闭到放射,最终形成圈域型经济圈,其城市规划发展与形成过程,为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圈发展带来不少启发。
因城市化时间早带来的市貌老旧是欧洲各城共同面对的难题。和英国一样,很多国家的发展策略是在老城区的外面规划、建设新城区,成功地实现旧城重建与新城开发的和谐统一。所以欧洲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会有很现代的商业新区,像法国巴黎西北部的新区就现代感十足。吸引了很多买不起市内昂贵住宅的巴黎年轻人不顾每日长途通勤,纷纷跑去那里安家落户,因为巴黎政府为市民建造了令人骄傲的地铁系统,免除了他们后顾之忧。
欧洲城市规划管理得好,主要原因还是有明确的法律作为依据,譬如英国政府就是通过诸如《绿带法》、《新城法》之类的法律予以支持城市建设,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圈的发展,也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带的形成。